
给我一碗羊肉,我就能跑完宁海50K
在坐高铁去宁海的路上,我心里慌得一比。这次是去跑50km组,但我之前仅跑过半马和20km组的越野赛。尽管夏天逼着自己在暑热的夜晚黑练,还增加了爬楼梯的练习,但实在是心里没底。特别是赛前最后一次LSD只跑了17km就因为脚背不舒服终止了。所以当时我看着车窗外连绵的田野心想,组委会真该设置报名的门槛,我这种没跑过全马但又手贱的人就不该出现在这趟开往宁海的地铁上。
出了高铁站,顺着志愿者的引导上了接驳车,看到里面竟然还有老人和胖子,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慌了。
“师傅,您也是跑50的啊?”我问一旁头发花白的大爷。
“哦,不,去年我跑了50,。这次呀,我跑100,也算是圆满了。”
“这位大哥,你难不成也是跑100的?”我又问一旁挺着啤酒肚的胖子道。
“那不敢。一年都没怎么跑了,去年50还能跑8个小时,今年目标就是完赛。”
突然我又觉得自己的心慌了起来。

(设在西门城楼的赛事大本营即终点)
领物十分快捷,检查完强制装备的大哥递还给我包,看了看我,鼓励道:“50k嘛,天黑之前就能把它干完了。”这口气,就像我跑步上班去单位时碰到从车里走出来的同事说话的样子:“不就5公里嘛,你们还开个车。跑个步也就半小时的事。”
坐公交车回酒店,没想坐过了站。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宁海人民医院,看到有人从救护车上径直被担架送了进去。心想,这一切不会都是安排好的吧。还没等我从缓过神,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奔腾骏马的酒店标志下。
9:30便洗漱完毕,盘点了一下第二天比赛用的东西,心里反倒平静了下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想象着自己在山野里奔跑的样子,很快就被自己潇洒的身影催眠了。在黑暗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被这个声音吵醒时,我突然后悔没有让前台给我换成背街的房间。抓过手表一看,才凌晨1:28。我试图平稳自己的呼吸,并告诉自己,别人吵别人的架,我睡我的觉。但是很快那个女人愤怒的尖叫声响彻了整条街道,然后是铁皮的撞击声。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脸上的口红和粉彩已经刮花,在惨白的路灯下拿着自己的高跟鞋疯狂地敲打着一辆轿车。车里坐着一个男人,面部扭曲,却岿然不动。突然那个声音渐渐地远去。我把那个女人从我脑海里请了出去,又开始想象自己在山里奔跑的样子。突然女人的声音又飘了回来,比之前更加歇斯底里。我看了一下手表,心中闪过一丝绝望。我迫切地盼望着有个男人出现,能制止窗外有些失控的局面。终于在2:30时分,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很快让那个女人恢复了平静。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又迷迷糊糊睡着。当我再次被吵醒时,是楼道里纷乱的脚步和几个年轻男子互相催促的声音。“WC,不会吧?这么早就出发了?”我心说,抓过手表一看,才4:48,距离我设定的闹铃还有22分。我努力地试着让自己躺在床上直至闹铃响起,但是当楼道里又一波脚步声响起时,我不得不从床上坐了起来,对已经清醒的自己说了一句: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西子国际的接驳车上总共才坐了5个人,其他4个人都靠在座位上打着盹,只有我默默地吃着面包、喝着牛奶,看着窗外的夜色慢慢被晨曦退去。车子达到岔路镇小学的时候,已经人头攒动。

(岔路镇小学即比赛起点)
我徘徊在人声鼎沸的教学楼,也想在人潮中卸下最后的负担,于是从一楼的厕所辗转到三楼,但里面的蹲坑都已被沾满,等候的人堵在门口,朝我摇了摇头。小学的厕所都是没有门的半开放式的蹲坑,无论多么豪华的准备,你都只能背在身上。所以每一排蹲坑就像是不同品牌背包的流动展示柜,从nathan到salomon,从UD到迪卡侬,从osprey到aonijie(排名不分先后),五彩缤纷,撩人眼球,只是那个味道和活人模特的姿势,实在有点,咳咳……
直到我走到四楼,才在一个背包撤离之后逮到了它留下的空位。还忘了交代一下,厕所里四个蹲坑共用一条排便池,末端的墙壁挂着一个水箱,只有拉下水箱的绳子,才会有水冲出把便池里的那个啥统一冲走。所以当我拉下绳子,看着汩汩的流水撞击前人的遗留激起巨大的水花时,内心的不安仿佛也被冲碎了。
从厕所里出来,沿着学校的回廊走向设在操场的起点,看到有人靠着柱子在吸最后一根烟,有人抓着栏杆在做最后一次拉伸,更多的人则在三五成群地自拍留影。舞狮队在操场上完成最后一道仪式后,所有人集结到塑胶跑道上,迎着霞光和破晓的朝阳举起双手,在蜂鸣的飞行摄影器的注视下,开始出发前的倒数。“三——二——一!”发令的汽笛声响过,热烈的声浪撞击着寒冷的空气,冲过校门,来到寂静的街道。

沿街的店铺卷闸门紧闭着,偶尔从窗户里探出几个脑袋,看着这群奇形怪状的人招摇过市。来到唯一的一个十字路口,已经有交警在维持秩序,将准备通过绿灯的大卡车拦在路口,我们则快速地通过红灯,怀着一丝的歉意告别了这一长队耐着性子等待通行的卡车司机。
镇上的街铺和水泥路漫漫从身后退去,几幢田边的二层楼房和一路目送我们吠叫的土狗过后,山的轮廓在眼前清晰起来。等跑完这条田间的小路,跨过不远处的石桥,就要上山了。而身边的人也有序地变成了一条长队,整齐的脚步声里夹杂着三三两两的闲聊。
“怎么冬天了地里还长着荷花?”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叫道。
“你脑残啊。这是莲藕好嘛。”另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纠正道。
“你他妈才脑残呢。莲藕不就是荷花吗?”1号眼镜男反驳道。
“等等,你说得对。”2号眼镜男思考了一会,说“这是芋艿。芋艿叶跟荷叶长得差不多。”
通往CP2的水泥路上,升起了动感的音乐,我以为是补给点的大喇叭里传过来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前面一个红衣大姐的背包里发出来的:
“月儿啊弯弯照我心
儿在牢中想母亲
悔恨未听娘的话呀
而今我成了狱中人
月儿啊弯弯照娘心
儿在牢中细思寻
不要只是悔和恨
洗心革面重做人”
我瞄了一眼头顶亮晃晃的太阳,迅疾把目光收了回来,对准了身旁的红衣大姐,只见她低着头,吐着气,伴着旋律踮着脚步,手上套着的银手镯发出了一道不屈的光芒。为什么呀,大姐,巍巍的高山和俊秀的苍野依旧让你忘不了广场舞的旋律?既然你那么甩不掉都市的生活,为什么不戴上耳机让周围人享受这份山林的宁静?你知不知道这么做,很容易拉开我和你的距离吗?
我快速地超越了还在踮着步的红衣大姐,顺着下坡的台阶,朝CP2跑去。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来:“朝我们跑来的是**号选手***。他步态轻盈,看得出胸有成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running hotel. 请允许我说一段英语,因为有一个国际友人朝我们补给站跑来了。”
这次比赛确实有几位国际友人。我还和其中跑得较慢的那个在竹林里有一段小小的对话。
“How are your shoes? Do they hurt?” 我指着他的那双nike路跑鞋问道。其实每次我超车经过跑友被他们叫做“大神”时,我心中总是惶恐不安的。因为真正的大神都是穿着路跑鞋跑越野的。
“They are alright.” 他满脸绯红,靠着一根粗壮的竹子喘着气。“just that I’ve never run this far.”
“Neither have I. I mostly run half-marathon. Never 50k.” 我也抓住一根竹子,大口地喘着气。
竹林里安静得只有喘气的声音。
我发现他身上只背了一个水壶,外套系在腰间。看上去就像是周末来爬山的游客。
“Take care.”我跟他告了别,心想,说好的强制装备呢。

(来周末登山的国际友人)
在CP3——我永远会记得CP3,就像我永远会记得初恋一样,等等,我好像忘了我的初恋是谁了……——因为我在CP3吃到了羊肉。这是越野赛好嘛,组委会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给我吃羊肉米线?我厌恶了都市生活的安逸和优渥,这回就想来好好地被大自然虐一虐,让疼痛和饥饿洗涤我那个越来越油腻的灵魂,可你却给我吃羊肉米线?算了,啥也不说了,大姐,能不能再给我盛一碗?大宝,你敢不敢明年继续提供羊肉,我拉我基友一起来报名?

我挺着肚子走出CP3时,心中无比羞耻,口腹之欲让我的灵魂又一次堕落了。但很快,在我经过竹林的一块路牌时,我那油腻的灵魂散发出了久违的光芒。
就如同每个小镇里都住着一个小芳,每场越野赛都有一个绝望坡。在宁海,这个绝望坡叫大短柱。刚看到大短柱的时候,心灵还是很受震撼的,因为坡度很陡,且都是碎石。
“你说那个女的讨不讨厌?真以为自己是谁呀。”身旁一个女的边爬坡边说。她头发染成了银色,手臂上的纹身随着摆动若隐若现。她身后一个用头巾扎着头发的男人伸出手,用力推着她的屁股。这个男的胡子染成了银色,手臂上也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纹身。
“不都是朋友介绍的嘛,一起来跑就拉进群了。”男的说。
“谁跟她是朋友啊。”女的说,“化的那个妆,一看就是个骚货。再说,她凭什么在群里用那种口气跟我说话?”
男的没有接话,几个跨步绕到女的身前,伸手接过她的手臂用力往上拉。
“我跟你说,等跑完这个比赛,我就退群。你也一起退群。”女的运气往上爬了一段,接着说,“我的屁股好酸啊,还有那个地方……”她瞅了我一眼,然后凑过去跟男的耳语了几句。
我突然觉得双腿充满了力气,几步就爬到了山顶。

(大短柱爬坡的起点)
CP4设在一个当地的祠堂里,当我迈过门槛,走进这栋四四方方的建筑里,一股巨大的安全感包裹住了我;而馒头、糯米团子和一些当地的糕点则是彻底让我空虚的胃幸福了起来。我摇摇晃晃走出祠堂,双腿竟有些懈怠。我绷起神经,告诉自己,终点有更多好吃的在等着我。
尽管只剩下了1/3的里程,但随着身体的疲劳加剧,接下去的山路显得漫长而又煎熬,每一个小小的爬坡都让我清晰地感受到身体里筋脉和骨骼之间的撕扯,以及由此牵出的痛苦。
“快,回个头,给大爷照个相。”
在我双手抵着双腿费力地爬坡时,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起初我还以为是身后陌生的男跑友开的玩笑,但紧接着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
“别逗了。人家可是100的冠军,赶路呢,有空理你才怪。”
什么?100K的冠军?我心里顿时剧烈地翻腾起许多模糊的词语,这些词语在感到一个身影从我身后靠近时瞬间集中在一起,汇成两个字“我操”。
他抄身经过,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扭过头,侧身给他让路,并看清了他的脸。这张脸我曾经许多次在网上各大媒体的文章里见过。我大叫了一声“闫飞龙!”他楞了一下,然后继续大步往上爬,不一会就消失在了转角的丛林里。我身体里突然涌过一阵热流,迅疾迈开了酸痛的双腿追了上了,追了几百米,除了小径深处的荒草,已没了人影。这个被我喊错名字的年轻人可是100km组的冠军啊,我瞬间知道了“业余爱好者和职业选手到底有多大差距”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和闫龙飞之间隔了多少碗羊肉米线?)
下山途中经过一个健身公园,便到了大溪滩边的景观道。此处的选手们像是散兵游勇,三三两两地迎着晚霞漫步,享受着终点前的平静和放松。几年不见的大学室友早已等候多时,一看到我,便从堤坝上翻身下来。“你不来宁海,我都不知道家门口还有这样的比赛。”
“你老婆呢?”
“陪我女儿在河滩边玩呢。”他越跑越快,“让我女儿也感受一下比赛的氛围。”
“明年一起报名啊。”
我俩说说笑笑,一起跑向了城楼的拱门。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不同见解,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来源:爱燃烧 — http://139.198.191.206:8081/diaries/382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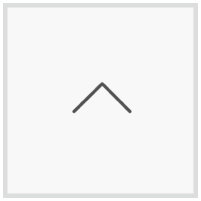

回应
回应
回应
加油加油!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