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线上的绿色小屋
快跑两步冲过终点线,按下表,抖去身上的冰渣,缓缓解开手腕上的杖带,在微微泛亮的晨光下看到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大家在飘着冰粒子的寒冬里等着我安然抵达。而此时的我径直走向最想见到的那个人,我等着一个充满着满满体温的拥抱。

随着身子一哆嗦,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做了一个梦,一个之前很久一段时间里在脑海无数次彩排过的场景。
而我现在正趴在一个老式的油汀上,脸和手牢牢地贴着在并没有热到发烫的油汀片上,身上盖着一块薄薄的被子,但是依然能感受到湿漉漉的衣服所带来的寒意。我赶紧看了一眼手表大约9点15分,我立马掀开身上的被子盯着身边的志愿者说:“I wanna go to finish line。”边说边能感受到嘴唇的颤抖,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试图证明自己还是清醒的。其实就在2,3小时之前,我应该是意识模糊的,在刺骨的寒风和冰雪中不断地在如溜冰场上一样的公路上摔倒和站起,同时清晨的阳光如利刃一般刺激着已然适应了黑暗的双眼,我几乎记不起来我是怎样翻过大帽山然后走过那段公路上坡和之后到救援小屋前的一段公路下坡。零星的记忆中,我尝试过双脚努力蹭开路面的冰渣前行,踩着路边冰冻的小草大步行进,甚至是坐在冰面上滑行,但是更多的是摔得四脚朝天,掩面扑街。
“比赛在5点就取消了。”一位义工说道。
“我要去终点,我可以走。”我带着疑问又一次说。
“你就在好好休息吧,比赛终止了,路都封起来了。”
我没有再说话,看到身边不断有被从赛道撤下来的选手进来。然后低下头从包里掏出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简单叙述了当下的情况,告诉说一切安好。
“你身体怎么样了,热了吗?”看似像这个小屋的主人的老人问道
“差不多了,我身体ok。”
“麻烦去里面的房间休息,把这个(油汀)给更严重的人吧。”
我起身拿上包来到内屋,里面没有暖气,只能裹上毯子坐在床角靠着墙。救护人员递给我两包瞬间制热的暖包,我便拉开外套放在胸口。然后渐渐地闭上眼睛,努力地回想这过去20多个小时里面发生的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
大约24日凌晨4:30到达CP9,看到许多人已经围坐在一个电烤炉的四周,有人微闭的双眼好像是在为最后大帽山的攀登积蓄最后的精力,有人端着热腾腾的食物努力让身体热络起来,更多的人则是忙碌地穿行在补给桌台和休息区之间为最后10公里整装待发。我就是其中一个,没有和别人有过多的交流,只是和几个跃跃欲试的跑友互相鼓励,大家都确信3个多小时完全可以到达终点收获一座小铜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大帽山已经不再是图片中看到的风景秀美的香港第一高峰,未知的危险也在一步步逼近此时正要上山的选手。两片面包和一杯热朱古力下肚,我在4点42分经过CP9的出站打卡点,跟着大约20来名选手一起走上大帽山,过了几分钟就明显感到了刺骨的寒风和愈加猛烈的冰雪,此时能做的除了把外套拉链收到最紧之外只有用最快的速度翻过这最后一座山。脚下的路也变成更加泥泞,有些大圆石踩上去已经开始打滑,只能选择石缝之间的泥地作为下脚处。所有人都排着一字长龙缓缓前行,耳边听到的全是冰粒子打在冲锋衣上面噼噼啪啪的声响。不一会,外套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冰了,一咬软水壶发现出水口也早已结冰。
按后来听到的说法,此时的大帽山已是零下。也在我出发后不久,凌晨5点,香港政府发出通知停止所有上山活动。而那时我脑子除了快点到达终点之外,几乎就是一个白痴,见路就上。在快达到山顶的时候,也许是在CP9吃的不够多,有点饿了,但是光秃秃的大帽山根本没有避风的地方,只能顶着强风用麻木哆嗦的手从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并极其困难地放入嘴中,然后继续赶路。
好在港百的路标极为清楚路线也非常成熟,低头看路也几乎不会迷路。就这样一路吭哧到了山顶,我觉得我还是幸运的,这时下大帽山的乱石路的一段还没有结冰,只是泥泞和湿滑,但是并不难走,集中注意不要去踩踏那些光溜溜的大石也不会有什么困难。唯一要对抗的还是呼啸而来的大风和打在脸上生疼的冰渣。
下到环山公路,心中一阵窃喜,以为剩下的路都是公路怎么样慢慢来都能在24小时内完赛,可是,毕竟还是太嫩,作为户外界的一员菜鸟最终马失前蹄,摔了个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在一段公路上坡已经隐约感受到了路面上结起来的冰霜,于是用脚蹭着地面的方式破开冰霜前行,或者走在路边已经结霜的草上。但是路面还是很快地结成了冰,不是每一段的路边都是有草地也不是草地总在一边,当要去马路另一侧草地的时候,由于大意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因为是上坡人还往下滑了一小段。不过总之还算顺利地抵达坡顶。
就下来便是噩梦的开始,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在鞋上绑上布条或是直接将手套套在鞋上。下坡一路几乎伴随的都是摔倒,起来,再摔,正摔,侧摔,仰面朝天摔,俯面贴地摔。身上的痛不说,眼角也在扑街摔时被眼镜框架刮出了血,左边的镜片也早也飞的不见踪影。这也是后来发现的,一度我以为自己摔的都已经天旋地转了,其实是因为少了一半的镜片。摔到最后干脆坐地不起,直接往下滑,好景不长还没滑多少路就被路边兴致勃勃上山赏冰的香港市民和救援队员给架下赛道拖入路边的一处小绿屋,我确信我一定有抵抗要求继续比赛,但是也许真的是摔的意识模糊还是这里被终止了港百之行。
这时,突然有人踢到了我的腿,我惊醒,由于里屋没有暖气还是可以感受并没有完全干透的衣服传来一丝凉意。这时看到一位全身早已被保温毯包裹住的老外躺在床上不停地颤抖,我又使劲地往角落里挪了挪,以便腾出更大的空间好让他把腿给伸直了。小屋的主人也过来把他脚上的湿鞋子给脱了并盖上厚厚的毯子。而此时整个小屋里面都已经挤满了人,救援队员准备开始要将恢复了一些状态的选手送下山去,但是只能步行,上下山的要道早已被60年才能见一次冰的香港市民的车给堵了,原来救援队也是徒步上山救援,这不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最好的写照么。
经过一轮询问有几个愿意下山的选手被救援队员搀扶着下山包括了一位刚进小屋不久的日本女选手,因为语言不通在一轮飞速的肢体语言后她重新穿上了羽绒服又一次扑进了寒风。其实我也应该是这一批下去的,但是当我走到门口时,一阵妖风将身体渐热的我又吹了个七荤八素,出门的小阶梯上也冻成了冰块了,我也毫不例外地又摔了,起身后赶忙钻进了小屋并在身上又多裹了一层毯子。
现在的我早已经不像从CP7到CP9的我了,之前不管是从赛记中看到还是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整个港百最难的爬升并不是大帽山而是之前的针山和草山,这17k几乎是整个比赛的魔鬼赛段,大量的爬升,身体的疲劳和夜间的困意,再加上寒潮也让众多选手在CP8,CP9纷纷退赛。赛前出发一起找了Sage Canaday合影的Fred也在CP8做出退赛的艰难决定之后还帮助其他选手进行了装备检查,不合格的都被他一一劝下免受后段赛程的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相比CP8工作人员的对于保温毯和手机的草率检查,要是请Fred做强制装备检查救援工作根本可以早早完成。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对于强制装备的要求不应该还是停留在原先的规定上,而是根据适当的情况升级对强行装备的要求,哪怕选手因为没有在赛事通知中写到而没带,也应该在CP8被劝停。

赛前嘚瑟地找了Sage合影。
相对于SP到CP3,我在CP7到CP9的状态更好,一是心理上的准备神经高度紧绷,二是已经习惯了这大风,而且自己装备也足以应付,更重要的是觉得我离终点更近了,过去几个月在脑子里无数次重复的画面即将呼之欲出。如果要我回忆出赛道和感受,几乎不能,也许看别人的赛记会有更多赛道的情况。我只是在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能跑的时候尽量多跑跑,累了就快走,眼前除了台阶还是台阶,纵使你怎么去挑土路最后还是接到台阶。而面对狂风能做的也只有想着快点离开山脊,只要有树就能挡住大部分的风。中间没能见到传说中的猴群,可能是我太慢了,猴儿们在白天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兴奋劲都回去睡觉了根本不愿再搭理我。
一路上几乎没有停留,唯一的大停留就是实在受不了脑门上国产头灯微弱的灯光换上另一款赛前刚从师傅地方拿来的国产胸前灯(其实国产头灯也是师傅推荐的,也经历过港百还去日本的UTMF),同样是国产,胸灯的亮度和视线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对比赛的信心,方圆3米之内无死角。也是在这一段开始产生了频频的幻觉,越是临近CP点幻觉越是强烈,前方稍微强烈一点头灯散发出的光源都会被大脑无限放大到以为是CP点发出的光芒。久而久之便不再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我看不清楚,反而更相信耳朵,志愿者加油的呐喊和CP点人群的声音都会让我抖擞精神小跑一段装作毫不费力地进入补给站并配合着志愿者报出自己的号码。
这时,小屋的主人拿进来一个怪模怪样的取暖器,长方形大约不到小腿那么高,通上电后也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温度,可能是太老了老得都忘了应该怎样工作,或许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样制热,反正这里是香港这些三角猫的功夫也能混混。内屋里的救援队员也越来越多,我猜是外屋有油汀比较温暖都留给了送山上撤下来的选手取暖。救援队员们也一个个冻的直哆嗦,屋内没有热水,搓热双手成了当下唯一的取暖方式。他们商量着救援对策,也不断对市民上山观雪堵车道的行为表示痛恨,因为所有的救护车辆根本没法上来救援。此时的我也对刚才没有下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后悔,然后询问着刚才那批队员何时回来,这样我就可以被护送下山了。连续的摔倒而产生的阴影让我完全丧失了独自踏着湿滑的冰面下山,和到达CP5之前大步流星下台阶时候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CP3之前的各种不想跑,抽筋和拖沓导致从CP4开始不停地在赶时间。在到达CP5之前最后一个下坡路上遇到了来接我的星星和加一,遇到他们的时候我正飞快下坡以至于都没有打上招呼,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下去就是企岭下的CP5了。CP4的志愿者告诉我从CP4到CP5有10K,到CP5是55k,导致我在下坡时瞄了一眼表51K多以为离CP5还有一段距离。到了CP5之后匆匆换上后半程的装备,已然知道银人无望但还是十分的焦躁,对于星星,加一和舒服在寒风中等待和不停地前后忙乎都没有说一句谢谢,明明就是一个跑渣却把自己当成了大明星,简直无地自容。在CP5还见到了大宝和追总,见到大宝时他早已全副武装准备陪人跑完后半程,而追总在豪华私补的照料下还悠哉地滚了泡沫轴。临出发前还蹭了追总豪华私补中的红豆沙,这也是全程中吃到的最好的食物。
离开CP5没多久天色就暗了下来,打开头灯进入夜间快速徒步模式,这时就看到追总双杖点地脚踏清风从身后超过,一溜烟就消失在黑暗中了。随即也开始小跑前行,尽管CP5到CP6是全程比赛中最长的赛段,但是现在想到也几乎毫无印象,秉承着有路就走的原则无脑地跟着山峦的起伏上上下下,马鞍山上的风大的差不多能将人都吹走,即使侧躺在风吹来的方向上也不会摔倒。山下远处便是星星点点的香港夜景,要不这阵阵妖风吹的脑仁疼,倒是挺想坐下来好好欣赏一番。到了基维尔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热食,泡面,咖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肚子里灌,此时的热朱古力毫不夸张真的已是淡如水,已经准备好接受甜味的肠胃突然被一阵白水冲袭,瞬间就产生了恶心呕吐的感觉,还好立马抓起傍边的巧克力压住了呼之欲出的苦水。之后到医务室在左脚的胫骨处打上绷带迅速前往笔架山。
这一段是我认为最为轻松的,或许是双眼和身体都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环境,前后的选手也没有交流一个跟一个机械般地运动,累了就站一边让后面的人先过一切都是那么的心照不宣。很快在一个小上坡之后到达了魔幻CP7,复古音乐加上火星四溅的火堆都会成为非常好的退赛理由。我吃喝完毕后本想在火堆边上取暖,此时已经有人在温热的环境下小睡过去,可是火堆的烟硬是把我熏出了眼泪呛出了鼻涕只能无奈离开。
同样是留着鼻涕的我,在小屋里的鼻涕却是被硬生生给冻出来的。我一边擦拭着鼻涕一边和一个貌似救援队队长的人聊了起来,得知救援的直升飞机由于飞到一半由于螺旋桨结冻又返回基地,所有的救援车辆依然堵在上山的路上,以及这真的是他们第一执行这样的任务。同时我手机回复了好友们关切的问候,不多时手机电量告急,匆匆给山下的星星打了电话再次报了平安以及告诉他们我会想办法下山之后切换到了飞行模式以保存电量以备不时之需。其实山上的信号一直断断续续,之后想问别人借电话但是都显示没有信号。
过不多时就被告知有救援队员可以护送我们内屋的大约5个人下山,没走出几步,由于种种的协调和安排我被暂时带到一辆救护车上,在车上依然打着寒颤,医生拿来了新的毯子又在我身上裹了一层。我还脱去了早已湿透的鞋子和袜子,双脚踩在厚实的毯子上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车内舒适的温度几乎让我又再次昏睡过去。突然有人打开车门一阵寒意让我突然意识到我还得继续下山。我试着用医生的电话给山下的星星和加一打电话,无人应答,我只能拜托医生一会再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经在下去的路上了。
就这样我匆匆穿上刚刚脱下的鞋袜,努力地将毯子裹得更紧,被救援队员牢牢搀扶着缓步下山。这就是我为自己CP4之前的拖沓和厌跑付出的代价,一直都认为前半程至少CP4之前很简单,如果没有狂风怒做的天气确实不难,路面的复杂程度也是完全可以接受。但是低温和寒风让身体极为不适应,在CP2之前两个大腿就分别抽筋了,好在路面相对平缓逐渐都得到了缓解。过沙滩时候的大风夹杂了沙粒只能选择低头摸瞎前行还一度走歪了方向差点走入沙滩深处,海滩上还不时飘过几阵死鱼的恶臭味道,心中无数遍发出真的热死也比冻死好的哀叹。
尽管有人扶着也不免屡屡在冰面上打滑,先不论香港警方,消防队没有没处理类似情况的经验,但是每一位救援队员或者说至少扶我下山的队员完全为这次救援行动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每当确定要摔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先倒下去,尽量让我可以倒在他的身上而不受更多的伤痛。等到了较为平暖,少结冰的路面,我被移交到另外两位队员手中继续护送我去扶轮公园,而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20小时后面还将面对更为繁琐的救援工作。他们一前一后将我慢慢地往终点送去,每当我问他们还有多久,答案都是5分钟吧,快了。在几个善意的五分钟之后,我看到了终点的拱门,四周一片稀稀拉拉,冠军冲线时候终点的热闹场景已经时大半天之前的故事了。
下午2点,我见到了我想见的人,我感觉到了她见到我时候的错愕,我也看到了她在一夜半昼焦急等待后脸上的憔悴。故事的发展远远偏离了剧本,内心的酸楚也大大超越了身体伤痛。我应该跑的快一点,我应该理智地早点退赛,种种想法都弥补不了我对星星的愧疚。在走向终点帐篷的路上也接受了香港记者们热情镜头的礼遇,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就在30小时之前的北滩涌,我们一行6人在起点合影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兴奋,毫无畏惧恶劣的天气一头扎入寒风中。我和三三也努力地站在了Sub16的尾端和Sub20的前端,静等比赛开始。15个多小时之后恭喜电鳗毫无悬念地赢取了小金人,17小时之后幕府也从此更名为银幕,23小时后三三和鞋霸也顺利将铜人收入囊中。

帐篷中,在星星和加一的照顾下换上了干爽的衣服,早已摔破相的脸在带上墨镜和拉上脖子上的头巾之后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这样在星星的搀扶下走出了大帽山扶轮公园。
再见,我的第一次港百。

看起来安然无恙。
在去往小巴站的路上,我想起了就在大概半年多前在狂沙漫飞的魔鬼城和一位朋友谈论起关于谢顶的问题,
我说:“我的后脑以后看来会谢顶。”
他说:“谢顶挺好的,要是我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说:“为什么啊。”
他说:“如果谢顶一定会发生那也没有办法,我就挺喜欢这样没有选择的人生,给什么样的路就跑什么样的路,给什么样的饭就吃什么样的饭。”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不同见解,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来源:爱燃烧 — http://139.198.191.206:8081/diaries/168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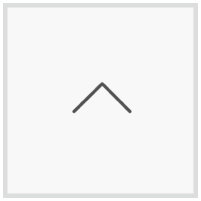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
回应